Avoice她视角丨《盐镇》中的女性生存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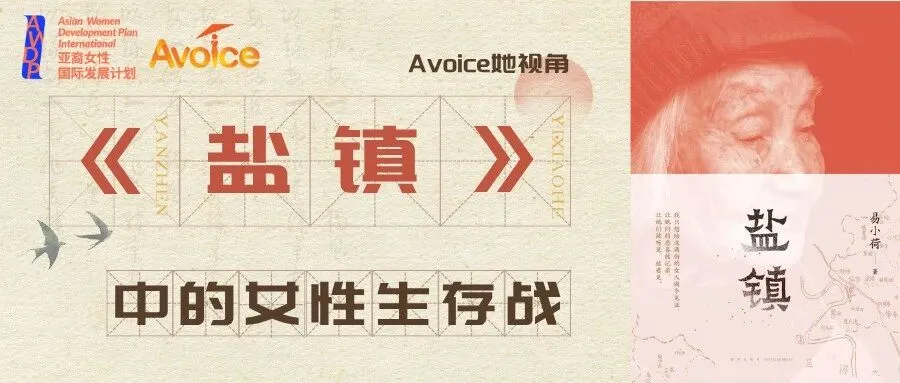
《盐镇》是记者出身的易小荷历时一年深入四川自贡一个古老盐业小镇所撰写的纪实作品。全书以年龄递减的方式串联起12位女性的人生故事: 从90岁的陈婆婆到17岁的黄欣怡,跨越数十年的时代变迁,却勾勒出惊人相似的命运轮回 。
作者:易小荷
她们默默无闻,终其一生被人忽略、被人遗忘,没有人知道她们如何存在、如何生活——不是她们不存在,而是她们被忽视、被遗忘。而易小荷以细腻而冷静的笔触、用写作揭开被遗忘世界的一角, 将乡土中国中那些默默无闻的女性命运一一打捞呈现。她强调自己并非只在写“女性之书”,而是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希望这些故事被更多人听见、看见、理解,促成改变 。
读完《盐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几段个人悲欢,更是一套深植于社会与制度之中的性别压迫结构。在这片土地上,女性如何在婚姻与贫困的夹缝中求生?在代际相袭的暴力循环里抗争?面对制度的冷漠与社会成见,她们又如何彼此取暖、自我拯救?
家庭暴力:
代际循环下的隐忍
在《盐镇》的开篇故事中,90岁的陈炳芝(陈婆婆)向作者讲述了她坎坷的一生。从童年起,家庭暴力的阴影便笼罩着她:父亲重男轻女,在母亲连生四个女儿后拂袖而去,将妻女抛入贫困深渊。 幼小的陈炳芝亲眼见证母亲独自拉扯几个孩子的艰难:上山挖野菜充饥、砍柴卖钱勉强度日,甚至穷到炒盐巴拌饭充饥。父亲的逃离既是经济上的抛弃,更是情感上的霸凌,这在年幼的陈炳芝心中埋下了深深的不安全感,也悄然开启了家庭暴力“代际循环”的恶果。
贫困如同沉重的阴影,限制了陈炳芝思考的能力,她在生活中前行的动力,似乎只是源自对动荡与不安的本能畏惧。因为深知“无依无靠”的苦难滋味,18岁的陈炳芝带着对命运转折的渴望,孤身踏上了谋生之路。她一心期盼婚姻能成为逃离困厄的出口,然而迎接她的却是命运更深的讽刺与伤害。生命中接连出现了三个男人,却无一人能成为真正的依靠。

第一个男人在她怀孕时弃她而去,她不得不四处漂泊唱戏。而就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年轻的陈炳芝挺着即将分娩的身躯,孤身一人迎来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没有亲人守候,她握着一把锈迹斑斑的旧剪刀,隔着土墙向邻居颤声请教如何剪断脐带。没有医护,没有灯光,只有隔壁婶子几句遥远的指点。那一刻,她亲手剪断的,不仅是孩子的脐带,更是对婚姻庇护的最后一丝幻想。
那一剪之下,是新生命的开始,也是旧命运的延续。几年前,母亲孤身生养的绝望场景再次在女儿身上上演,仿佛命运在沉默中完成了一次残酷的轮回。婚姻未能成为港湾,反而成为了将她推回原点的风暴。
第二任丈夫张运成是个酗酒成性的渔民,疑心重,常因陈炳芝与人交谈就暴力相向。她曾被他拖拽殴打,头被砸进咸菜坛,血流满面。她说:“每次打,他都能扯掉我几撮头发。”
镇上人对此无动于衷,家暴被镇上人视为稀松平常的“家务事”。有一次,她产后七天仍在坐月子,就被丈夫从床上拽下痛打。缺乏法律干预和舆论支持,让她陷入“殴打-逃离-和解”的恶性循环。直到张运成意外去世,这场旷日持久的伤害才得以终结。
令人唏嘘的是,陈炳芝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盐镇,许多女性的人生轨迹都在重复着类似的命运:书中一位媒婆,即便明知丈夫有家暴前科,仍在威胁与无助中选择复婚,像无数人一样,再次踏入那条早已浑浊不堪的河流。
上一代女性的创伤,往往在下一代身上悄然延续,不只是家庭结构的复制,更是性别观念的深种。 父亲的离弃、丈夫的殴打,源于乡土社会根深蒂固的父权秩序。当暴力被视作“家务事”而沉默,它便成为一种无形的“遗产”,在代际之间悄无声息地流转。她们被困在命运预设的舞台上,一幕幕悲剧按部就班地重演。
性别不平等的生存困局:
穷途末路下的抉择
家庭暴力的根源,远不止于个体的暴戾与愚昧,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教育与经济资源的长期不平等,将底层女性推入无力自救的困境。 陈炳芝只上过几天学,甚至认不全自己的名字。缺乏教育让她注定无法进入体面行业,只能靠体力劳作糊口:年轻时在茶馆做杂工,后来为养活五个孩子,做起了粮站搬运工——扛的是沉重的麻袋,换来的却是微薄的工钱。
在盐镇,性别差异从一出生就决定了命运的走向。女孩读书机会稀少,挣钱的路径狭窄,而婚姻则被迫承担起经济跳板的角色,成为她们唯一的出口——看似是出口,却通往另一场困局。陈炳芝正是带着这份微微的希望投入婚姻,却发现所谓“好人家”,只是一种无法兑现的承诺。
当婚姻无法庇护,反而成为新的牢笼,女性便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离开,可能一无所有;留下,就要忍受暴力与压迫。
这种困局在《盐镇》中屡见不鲜。一些女性即便初步经济独立,依然不敢轻易离婚,只因社会对“离异女人”满是偏见与审视。书中那位看似风光的女强人,事业上八面玲珑,却因恐惧舆论、抚养压力等种种现实,只能苦苦维系一段早已破败的婚姻。可见,在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下,婚姻并不总是避风港,有时反倒与贫困一起,成为女性身上的双重枷锁。
在如此逼仄的生存空间中,一些女性不得不做出极端而艰难的选择。《盐镇》中“猫儿店”的故事,令人唏嘘。“猫儿”,是四川自贡一带对性工作者的俗称。58岁那年,陈炳芝无奈开起这样一家“猫儿店”。最初她只想卖茶糊口,无奈生意惨淡。镇上的牛贩黄居光见她独自养活一群孩子,出主意让她改行。没过多久,一些年纪偏大的中年妇女找上门来,由她提供食宿,以出卖身体换取家中生计。
这些“猫儿”大多是走投无路的妇人,上有老母、下有稚儿,全靠自己维持生计。她们年纪不轻、姿色不再,在城市边缘无法立足,只能退而求其次,来到这间简陋的小店。陈炳芝理解她们的不易,每单只象征性收五元佣金,若无人上门,便分文不取,甚至包一日三餐。街坊邻里视她为赚“昧心钱”的老鸨,私下冷语戳骨;可在那些在风雨漂泊的女人眼中,这家小店是难得的庇护所——不仅换来活命钱,也换来尊严。
透过“猫儿店”这扇真实的窗,我们得以窥见底层女性绝境求生的方式。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现实并未随着时代的更迭而消逝。21世纪的盐镇,一位年逾九旬的老太太和一位年仅17岁的少女,居然在从事着相同的皮肉生意。陈炳芝靠收留性工作者拉扯孩子长大;黄欣怡这样的00后少女,辍学后在KTV坐台,被所谓的“男友”带入灰色世界。不同年龄,不同年代,却上演着相似的命运。
到底是什么,将一代代女性推向同一个深渊?
是那根植于制度与文化深处的性别不平等。当教育的门槛高高立起,当体面工作的机会对她们半掩着,当婚姻不再是出路、社会保障缺席,她们只能在有限的选项中挣扎求生。有人选择忍耐,有人选择铤而走险,无论哪种选择,背后皆是沉重的命运。
正如书中所写,她们的人生仍在重复着古老的轮回:困于婚姻,困于贫困,困于不被看见的命运。这不只是个体的不幸,更是一种沉默而漫长的群体疼痛。
暴力的循环不是性别使然
而是系统使然
《盐镇》中有一个静默却撼人的故事——关于两个女人的爱与困境。童慧,年届五旬,年轻时容貌出众,终身未婚;红梅,中学教师,有过短暂婚史与一个儿子。在小镇如铁的目光中,她们彼此靠近,以一种对抗世俗的姿态共同生活。人们讳莫如深地称她们为“女同”,她们却在沉默中编织出一段只属于彼此的柔软岁月。
起初,人们以为她们的结合是一种逃离,是对男性权力结构的温柔抗议。然而时间缓缓推移,那些深植于骨血的父权幽灵,悄然回到了她们之间。红梅逐渐习得镇上男人的恶习:酗酒、赌博,将愤怒以拳头表达。而童慧,则成了沉默的承受者——像无数被命运钉在厨房与卧房之间的妻子,在红梅酒后的辱骂与暴力中一言不发,将泪水吞进黑夜。
她们的争执,像极了被套用过无数次的旧剧本:谁该管钱,房子写谁的名字,父母和孩子由谁照料……那是无数“夫妻”之间的琐碎日常,如今却在两个女人之间重演。原以为爱能带来解放,最终却变成了另一种禁锢。
这段关系的崩裂,并非因为她们是女人,而是因为社会早已为“亲密关系”预设了某种格式:一方掌控,一方服从;一人开口,一人缄默。在这套剧本中,性别只是扮演角色的门票,而真正决定结局的,是权力的结构与文化的脚本。红梅并非天生粗暴,而是被教会了如何成为“强者”;童慧也不是生来软弱,她只是太熟悉那个“逆来顺受”的模样,哪怕换了舞台,依旧知道何时低头。
她们的亲密关系并未摆脱传统脚本,反而在无形中重复着。哪怕舞台上不再有男性,社会对于“谁该主导、谁应服从”的期待仍在——只是这一次,角色由两个女人分饰。那套看似属于异性婚姻中的性别分工,并未因性别构成的改变而被打破;它如幽灵般缠绕其中,将本该解放的关系再次拖入权力的博弈之中。
当红梅举起酒瓶,发泄怒火,她扮演的是制度设定的“主导者”;而童慧则躲进沉默与隐忍,她只是延续了被驯化的“附属者”的姿态。在这场无声的拉扯中,爱变得面目全非,暴力的剧本清晰可见。
这场关系的破裂,最终并不源于她们的性别,而是源于一种早已内化的结构惯性:谁主导,谁让步;谁说话,谁沉默。亲密关系仿佛被某种既定的模式牵引——即便换了组合,剧本依旧熟悉。真正伤人的,从来不是谁变了,而是女性从未有过逃离暴力剧本的机会。
女性互助:
在黑暗中点灯
尽管《盐镇》书写了众多女性命运的苦难与挣扎,但在压抑与沉重之间,也潜藏着女性之间守望相助、自我救赎的温柔光芒。
陈炳芝就是这光芒中的一束。丧夫后,她没有再依赖任何人,而是独自抚养了五个孩子,靠当搬运工和在茶馆打工度日,最终无奈开起“猫儿店”维生。世人或许不理解她“赚昧心钱”的行为,但她却用这家小店庇护了一群走投无路、被社会抛弃的女性,象征性抽佣、管吃管住,雪中送炭,扶持他人度过难关。在世俗眼中,她是“老鸨”;在被困女性眼中,她是能暂避风雨的港湾。
陈炳芝的坚韧不是孤例。《盐镇》中的女性,在缺乏制度庇护的夹缝中,往往只能彼此托举,点亮彼此。她们以最微弱但最真切的方式进行抵抗:有人选择留在困境中默默承受,有人尝试走出小镇谋生,更有人在沉重的日常中悄然觉醒。
正如易小荷所写: “当你以为自己已到谷底,会发现谷底早有人在,她们的生命力将你往上托举。”这些不起眼的互助,不似革命那般轰烈,却是一束束透过铁幕的光,照见了希望,也照亮了彼此的路。她们没有放弃生活,而是在命运的洪流中,用倔强和温情,撕开了一道光的裂缝。
当她们呼救时
谁在听?
《盐镇》中最令人心酸的一幕,不是苦难本身,而是那些苦难背后空无一人的街巷。书中女性一次次站在生活的边缘,伸出求救的手,却很少迎来制度的接纳与社会的正面回应。她们的困境,既源于个人命运的沉浮,更深植于对女性冷漠以对的结构性沉疴。
首先,是制度之手的迟缓甚至缺位。在那个年代,家暴不是罪行,而是“家务事”;打老婆不是违法,而是“男人的脾气大”。年轻时的陈炳芝被丈夫拳脚相加,邻里却只劝她“忍一忍、就过去了”;而制度并未给予她任何庇护。
即使如今,《反家庭暴力法》早已出台,但在偏远乡镇仍缺乏执行力,基层缺乏庇护所与专业心理支持,触及不到急需援助的女性。书中那位曾逃离施暴丈夫、最终又复婚的媒婆,并非因为爱情,而是因为“离婚比结婚难活”。制度与社会支持的空白,让女性在逃离暴力后跌入了更大的深渊。
遗憾的是,法律面前,那些生存已成难题的女性,没有被救助,而是被惩罚。晚年陈炳芝因收留几位中老年贫困女子“出卖身体”被定罪,每月的低保被取消。打击非法行为固然有法可依,但不考虑和解决现实情况的照本宣科,只会让弱者更弱、底层更沉。在这场清算中,男人无声无影,仿佛从未存在过。女性的身体成了靶标,男性的责任被悄然掩盖。这是偏见,而非正义。
更冷酷的,是人情的麻木。陈炳芝晚年被骗光积蓄,只因错认一位陌生女子是自己早年失联的小女儿。她的信任源自母爱本能,源自内心深处尚未被彻底熄灭的温情。但邻人对此毫无怜悯,只冷笑着说她“活该”。他们选择遗忘她曾如何为五个孩子背水一战。他们只记得她曾开“猫儿店”,将她的苦难归因为“咎由自取”。同样的冷漠也投向童慧和红梅,她们始终被当作异类,童慧在多年后仍无法坦然说出“我们是一对”这样的话。在盐镇,女性的选择若不符合“贤惠、节俭、隐忍”,就要被贴上标签,连落难都不值得怜悯。
表象的背后,是更深层的、结构性地忽视:女性的声音被湮没,女性的痛被常态化,女性的不幸被当作“命该如此”。当制度迟迟不来,那些呼救像落入井底的回音,越来越远、直到无人问津。
《盐镇》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无数女性命运的轨迹。它让我们看到:性别不平等并非一场偶发悲剧,而是系统性编排。当苦难被看作常态、被归咎为“活该”,真正缺席的,是理解,正面回应,与改变。而写下、讲述这些故事,让更多男性和女性看见和理解,正是打破沉默、促成改变的第一步。
撰稿|潘韵仪
编辑|Jane
封面/排版 |池一诺
图片|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