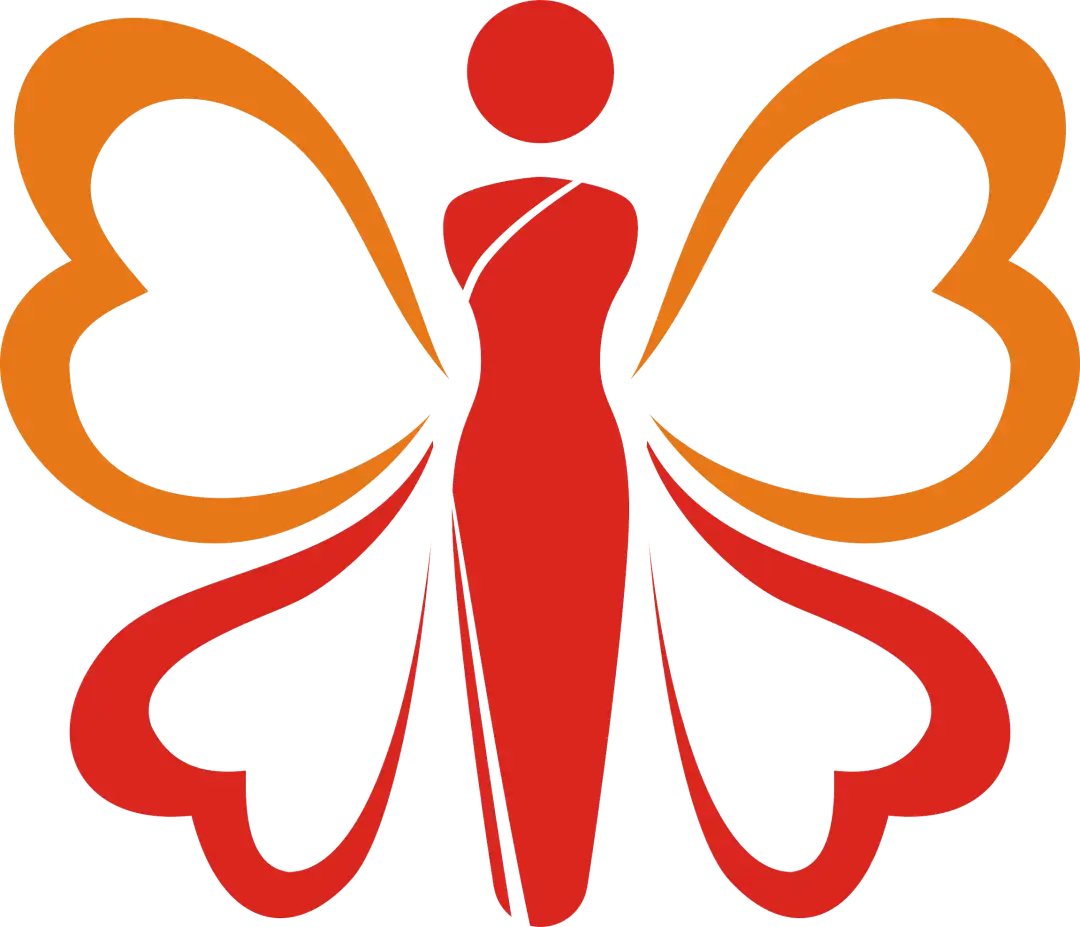Avoicer-Ta⼒量|AWDPI 2024年度优秀志愿者纪实(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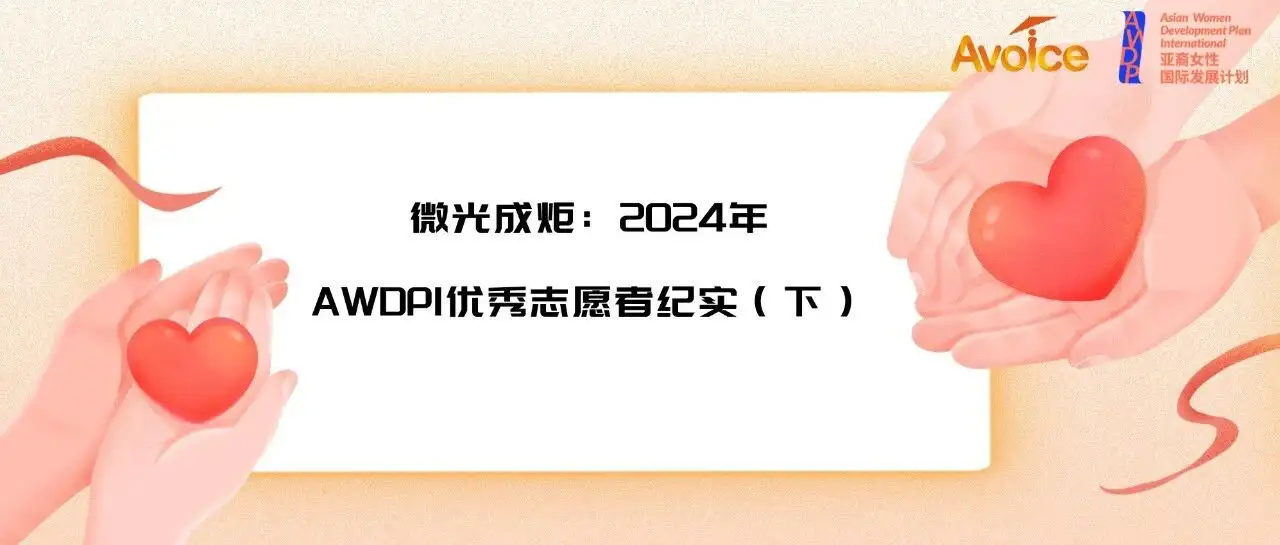


今年正值AWDPI(亚裔女性国际发展计划)成立五周年。
自2020年创立以来,AWDPI始终致力于消除针对海外亚裔女性的性别歧视和性暴力,构建跨国救助支持体系,推动社区赋能与倡导。五年来,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了这一场温暖而坚定的行动,用陪伴与倾听,为幸存者点亮重建未来的微光。
在前两篇内容中,我们看见了志愿者们对于救助工作的坚守,对自我性别意识的不断反思和重构,以及对珍贵女性情谊的呵护。
本篇作为本系列文章的终篇,我们采访了两位身处一线,能够与性暴力幸存女性直接互动的志愿者。 她们用前线的救助经历为我们勾勒出“反暴力”以及“跨国救助”面临的实践困境,以及她们如何接纳挑战,把“反暴力”的宗旨和口号化为切实落地的力量。
让我们继续走近这群以微光成炬的同行者。

心理处外联 王乐怡
从事志愿服务近一年半
“从倾听和沟通中找到她们真正的需求。”
在外联处的工作中,我的核心任务是接洽前来AWDPI 寻求帮助的来访者。她们被接入后,我们会有一个团队为她们匹配合适的咨询师,陪伴完成心理咨询与支持服务。

个案对接处 勾勾
从事志愿服务近一年半
“我们无法立刻改变整个体系,
但可以通过个案积累推动长期变化。”
个案工作的工作流程从求助人接触线上小助手开始。小助手是求助者第一次联系组织时的主要接洽人,小助手会初步了解求助者的诉求,同时提供一个安全的倾诉空间。
✦
•
✦
这一系列专访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但属于AWDPI的故事,属于每一位志愿者的故事,属于每一位在海外生活的亚裔女性的故事仍在继续。

撰稿|孔令雯
编辑|伊哲
排版&封面|杜婉婷
图片来源|unDraw